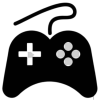关于教育,东西方有着不同的定义。东汉许慎编著的《说文》对“教育”两字是这样定义的:教者,上所施下所效也。育者,养子使作善也。
西方人的教育是education。从字源上看,词根duct-表示“引导”的意思,前缀e-表示“向外”的方向,后缀-tion表示“名词”的词性。由此可见,把人的本性或者天赋向外引导出来的行为,就是西方人理解的education。
由字面定义可以发现,西方人的education基本上等同于中国人的“育”,而“教”,在西方人的概念中,是基本空缺的。这就是东西方教育的根本性区别所在。“教”到底是什么?中国人常讲尊师重教;养不教,父之过,教不严,师之惰;有教无类;良好教养等等,为什么中国人这么重视“教”?“教”到底是指什么?我们继续往下看。
古文的“教”,左上一个爻,左下一个子,表示让小孩开智;右边是个攵,古时指小棍棒。也就是说,让孩子开启智慧,童蒙养正,一旦偏离了正道,就要用小棍敲打使之重新回正。就像小树苗,长歪了就要随时扶正,并及时修整,使之最终成才。所谓“上所施下所效”,个人理解有两层含义,其一:施教者(家长、老师)怎么做、怎么说、怎么想,受教者(孩子、学生)就会效法模仿成什么样;其二:施教者实施、施行到什么程度,受教者就会达成什么效果。
所以,我们中国人的教育是分为两个方面来进行的,即做人的“教”和成才的“育”。
中国人的教育讲究先成人后成才,教为本,育为末。而西方education偏重成才,缺失做人。为什么?因为古代中国人的教育是严格遵循士、农、工、商的合理顺序进行的;西方人认为人是会使用“工具”的高级动物,所以西方的education,是朝着把人打造成“工具”和“高级动物”的偏路上进行的。人,首先是个人,而不是动物或工具。人者,仁也,核心也。天地阴阳二气相合,得其正气者为人,得其偏气者为兽。中国横跨北纬30度,地形各异,气候适宜。因此中国人相对更正,天性更仁爱。而外国人,古称蛮夷,偏盛之气相对过重,因此天性离“仁”较远。
东方的教育,历来讲求动静结合,刚柔并济,德才兼备,品学兼优,做人为本,做事为末;西方的education,忽视前者,强调后者,只重头脑,不见心灵。
目前学校开设的三门主课“语数外”,其实都是语言,语言是一切学科的基础。其中,语文是中国人的语言,外语是西方人的语言,数学是机器人的语言。既然都是语言,三者是什么关系呢?——并非我们以为的横向互补关系,而是纵向源流关系。一言以蔽之:中华文明开创了西方文明,西方文明开创了器物文明。如果把人类文明比作一颗大树,中华文明是根干,西方文明是枝叶,器物文明是花果,人工智能则是器物文明开出的一朵奇葩。如果按照东方的“教育”,把人当作真正的人来培养,则不必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而担忧;假如按照西方的education,继续把人当成机器或动物去训练,即使孩子再牛,未来也即将面临被AI替代的窘境。因为一个人的力量再大,也干不过一台机器;一个人的左脑再快,也比不过一台电脑。代差在那儿,降维打击不可避免。
智能机器崛起,让数理逻辑能力不再有优势; 欧洲美国衰落,让外语沟通能力不再有优势; 中华民族复兴,让中华传统文化重新有优势。
学好数理化,走遍工业时代都不怕; 学好英美法,走遍信息时代也不怕; 学好圣贤文化,走遍智能时代才不怕。
我们已经经历了AP(artificial physical)阶段,人工体能取代人类体能——身的20世纪。
我们正在经历AI(artificial intelligence)阶段,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智能——脑的21世纪。
未来,我们也许还将经历AS(artificial spirit)阶段,人工灵能取代人类灵能——心的22世纪。
世风渐转,正气回归。眼前的教育之路,一条是正道直行,一条是末路狂奔。这世上本就有道,走的人少了,也就隐了道。这世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。希望正道直行的人越来越多,重新回归本属于我们自己的那条生存之道和教育之路。